漢朝可以再次中興,晉朝和宋朝也是兩朝,為何沒有辦法再次崛起呢
漢朝中興本就是劉秀集團(tuán)編織的謊言!兩漢與兩晉、兩宋也完全不是一個概念,如果用“粗糙”的說法下一個結(jié)論就是:歷史上沒有一個王朝可以做到在滅亡以后再次崛起,晉、宋如此,漢也是如此。
為什么說“漢室中興”就是個謊言呢?理由很簡單,所謂“中興”是指一個王朝走到低谷之后二次崛起,其中暗含一個條件——該王朝是一個連續(xù)的、有繼承性的政權(quán)。東漢與西漢連續(xù)嗎?有繼承性嗎?顯然沒有。而東晉和南宋,確實(shí)是對西晉和北宋的繼承,是一個連續(xù)的王朝。
西漢從漢平帝元始五年(公元5年)駕崩后,王莽立宗室子弟劉嬰為太子,自任攝皇帝。始建國元年(公元8年),王莽受禪登基,改國號為“新”,西漢滅亡。
地皇四年(公元23年),綠林軍建立自己的政權(quán),國號也叫“漢”,皇帝叫劉玄,史稱“玄漢政權(quán)”,或“更始政權(quán)”。當(dāng)年他們攻破長安,殺掉王莽,新朝滅亡。
更始三年(公元25年),劉秀在河北鄗縣稱帝,他所建立的政權(quán)也叫“漢”,史稱“東漢”。同一年劉玄被赤眉軍殺害,玄漢政權(quán)滅亡。當(dāng)時赤眉軍也建立了一個“漢”政權(quán),皇帝叫劉盆子,后來被劉秀所滅。
看清楚沒?劉秀的東漢與西漢中間隔了一個新朝和劉玄的漢朝,根本不連續(xù),也沒有任何政治上的繼承性。也就是說東漢和西漢其實(shí)是兩個毫無關(guān)聯(lián)性的獨(dú)立政權(quán),不存在繼承關(guān)系,更不是一個政權(quán)。既然如此,請問“中興”何來?
劉秀是東漢開國皇帝,但他一直宣稱自己是子承父業(yè)的中興之主,我戲稱劉秀是,“主動放棄王健林這個創(chuàng)業(yè)者的光榮身份,而選擇了王思聰這種富二代的身份”。
為此劉秀咬牙吞下了苦果,他把自己過繼給了西漢漢元帝為子,他的親爹劉欽則從法理上與劉秀斷絕了父子關(guān)系,沒有獲得追封為帝的殊榮。其實(shí)漢元帝比劉秀大69歲,劉秀出生時漢元帝都已經(jīng)去世27年了。
劉秀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個:要讓后世認(rèn)為他的“漢”就是西漢的“漢”,而不是新政權(quán),因此他只能做繼承者,而不是開國皇帝。
劉秀為什么不能做開國皇帝?因?yàn)楣湃苏J(rèn)為,王朝更迭要有天命,假如劉秀說自己是創(chuàng)業(yè)者,對不起,請你拿出老天給你出具的合法證明,否則你的政權(quán)就不合天命,就會被老天厭棄。
這東西今天看起來很搞笑,但在古代是個很嚴(yán)肅的法理問題。劉秀沒法證明,最簡便的方式就是告訴世人:俺也沒說我這是新政權(quán)吶,俺從祖宗手上繼承的,是富二代,至于西漢的合法性還用我來證明嗎?
因此,“漢室中興”就是個謊言,我們只能說劉秀建立的王朝,把中國的歷史再次拉向一個新的高潮。我們不能因?yàn)閯⑿闶莿畹暮笕耍驼J(rèn)為兩漢一體,更不能一廂情愿地認(rèn)為漢朝再次崛起。
再談第二個話題:王朝的中興全都是曇花一現(xiàn),從來沒有真正的二次雄起,晉朝、宋朝如此,漢朝也是如此。
我們熟知的百年王朝,其發(fā)展軌跡有個共性:開國頭三代皇帝銳意進(jìn)取,國力大增,進(jìn)入大治時代。到中期后,皇帝昏庸無能,高層權(quán)貴腐敗墮落,社會矛盾加劇。這時候大多會出現(xiàn)一兩位所謂的中興之主,他們大刀闊斧割除弊政,王朝出現(xiàn)新氣象。但中興之主一駕崩,王朝立刻進(jìn)入不可遏制的下行道,以加速度的方式滅亡。
每一位中興之主就像夜空的禮花,把自己的絢麗留在了史冊,卻在身后留下一地雞毛。問題來了,中興之主為何不能再造乾坤,讓發(fā)展的勢頭持續(xù)下去,卻成了王朝衰敗的分水嶺了呢?我們以晉朝和宋朝為例說明。
首先,東晉和南宋的命不好,他們面臨不光有“內(nèi)憂”,還有“外患”
東晉的第一任皇帝司馬睿,是司馬懿的曾孫,15歲時繼承了瑯琊王爵位。“八王之亂”后期,司馬睿奉命出鎮(zhèn)揚(yáng)州,一大批北方豪族勢力跟著他南遷,史稱“永嘉南渡”。
建興四年,匈奴人劉曜攻破長安,晉愍帝出降,西晉滅亡。第二年,司馬睿在南遷的豪族勢力擁戴下,在建鄴稱“晉王”,晉愍帝被殺后,他又登基稱帝,延續(xù)了司馬家族的基業(yè)。
南宋第一任皇帝趙構(gòu),是宋徽宗的第九子,宋欽宗的弟弟。靖康之變爆發(fā)后,北宋皇族被“團(tuán)滅”,京城的皇族子弟全都被打包發(fā)配黑龍江。
趙構(gòu)成了唯一的漏網(wǎng)之魚,那時候他受命天下兵馬大元帥,出京招募勤王之師,碰巧不在開封。金國人撤退后,留下張邦昌為“大楚”偽皇帝,替他們鎮(zhèn)守中原。可是張邦昌不愿意當(dāng)漢奸,金國人一走他就主動讓出皇位。于是趙構(gòu)撿了個漏,在應(yīng)天府(商丘)登基稱帝,續(xù)上了趙宋天下。
東晉和南宋雖然延續(xù)了“天命”,但他們面臨的環(huán)境非常惡劣,可謂內(nèi)憂外患交加。
東晉南遷后首先面對著政治基礎(chǔ)薄弱的問題。司馬睿出身皇室庶支,在法理上遭到宗室的質(zhì)疑。作為晉朝統(tǒng)治基礎(chǔ)的山東士族集團(tuán),雖然大量南遷,但相對于江南士族集團(tuán),他們畢竟是外來客,如何融合兩大士族集團(tuán)是個大問題。另外,衣冠南渡之后,以王敦為首的軍功勢力與皇權(quán)矛盾激化。
這三大內(nèi)憂,整個東晉都未能解決,它最終也亡于這些矛盾的爆發(fā)。
此外,東晉還面臨著北朝的威脅。從軍事實(shí)力上講,東晉與北魏無法相提并論,倘若不是北魏自己出了問題,東晉恐怕早就被滅了。
南宋建立后也同樣如此。搞垮北宋的政治毒瘤黨爭問題始終不能平息;崇文抑武的國策不能適應(yīng)現(xiàn)實(shí)需求,導(dǎo)致南宋常常自斷手臂;南方的富庶又滋生了朝廷偏安一隅的墮落心態(tài)。
倘若不是金國的鐵蹄,南宋皇帝們活得相當(dāng)滋潤,根本無視懸在頭頂?shù)牡秳ΑK^中興,收復(fù)失土是起碼的條件,軍事實(shí)力的差距,讓南宋大多時候連過江的心思都沒有。同樣,如果不是因?yàn)榻饑俗约撼隽藛栴},南宋不可能支持那么久。
劉秀當(dāng)時面臨的環(huán)境則要簡單得多,起碼他沒有外患,那時候的匈奴元?dú)鉀]有恢復(fù),鮮卑還處于初階階段,西羌只會小打小鬧。那時候的南方人口稀少,經(jīng)濟(jì)不發(fā)達(dá),其政治影響力有限,因此劉秀的主戰(zhàn)場主要在中原和河北。
當(dāng)然,我不是說劉秀的難度小,但不得不承認(rèn),他所面臨的環(huán)境相對于東晉和南宋要好得多,沒有不可跨越的障礙。
其次,東晉和南宋第一任皇帝上位,靠的是“顏值”,而不是“能力”
中興之主是王朝中興的靈魂,卓越的才華和出色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,這就是開國之君往往成為后人楷模的原因。很不幸,司馬睿和趙構(gòu)都是“富二代”,與從白丁出身,一刀一槍拼殺出來的劉秀完全不是一個檔次。
司馬睿雖然是東晉開國之君,卻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庸主,他在位只有六年就被郁悶死了。六年間司馬睿只做了一件事——對抗王敦,可惜他既不能正確評估自己的實(shí)力,又不能有效利用王敦的反對勢力,結(jié)果成了王敦的俘虜。
后世對司馬睿的評價,除了承認(rèn)他“仁厚”外,幾乎沒有一句好話。其中尤以魏收的評價最犀利:“竊魁帥之名,無君長之實(shí),局天脊地,畏首畏尾,對之李雄,各一方小盜,其孫皓之不若矣。”
就連對司馬睿最忠心的王導(dǎo),都說他“名論猶輕”。
趙構(gòu)要比司馬睿強(qiáng)很多,在靖康之難中,他所展現(xiàn)出來的勇氣,一度讓人我們恍惚看到了一個高大的身影;他對秦檜、張浚、劉世讓能人的擺弄,讓我們看到了作為他政治家的高超手腕;他對岳飛的狠毒,也顯示了他最為皇帝的厚黑。
但是,這些顯然遠(yuǎn)遠(yuǎn)不夠,他不具備撥亂反正的英武之氣,也沒有胸懷天下的大氣磅礴,更缺少克復(fù)中原的民族擔(dān)當(dāng),在他狹隘的心里,個人利益始終在第一位。
作為溫室里長出來的花朵,司馬睿和趙構(gòu)天生就是“顏值擔(dān)當(dāng)”,經(jīng)歷風(fēng)霜的能力不及常人,根本不具備中興之主的能力。
對比一下劉秀,人家童年就跟著父親、叔叔四處漂流,成年后讀過太學(xué),又跟哥哥一起混跡江湖,自己養(yǎng)了很多江湖俠客。其知識面、社會實(shí)踐、解決問題的能力,以及對社會問題的認(rèn)知水平,遠(yuǎn)不是司馬睿和趙構(gòu)所能比的。
最后,作為繼承者,他們的操作空間上限是“改革”,而不是“革命”
所謂中興為何不長久?仔細(xì)研究您就會發(fā)現(xiàn),他們的中興之路無外乎兩個字——改革,通俗一點(diǎn)講就是修修補(bǔ)補(bǔ),砍掉某些阻礙社會發(fā)展的主要既得利益人,讓底層百姓的創(chuàng)造力得以發(fā)揮。
但這種改革往往是避重就輕,沒辦法徹底鏟除弊病之根,往往中興之主剛剛駕崩,舊勢力立刻抬頭,所有的改革成果瞬間被推翻。
中興之主們?yōu)楹尾弧案锩保浅洚?dāng)補(bǔ)鍋匠呢?不是不想,而是不能!
任何一個政權(quán)都需要政治勢力的擁護(hù),而這些勢力在擁護(hù)皇權(quán)的同時,同行一定會轉(zhuǎn)化為阻礙社會發(fā)展、掣肘皇權(quán)的反派力量。這種兩面性讓中興之主們很為難,“革命”就意味著推翻重建,也就等于把自己的擁躉推向?qū)α⒚妫秦M不是自掘墳?zāi)梗?/p>
這就是所有“顏值擔(dān)當(dāng)”們的煩惱,他們身處利益的漩渦,各派政治勢力與他們利益犬牙交錯,一刀下去傷別人也會傷自己,這刀很難下!
可是開國之君沒這個煩惱,前朝的所有勢力與新生力量本來就是利益對立面,雙方見面就一句話——干就完了!
因此,劉秀可以革命,司馬睿和趙構(gòu)只能改革。比如司馬睿,原想“革”王敦,結(jié)果被人家“革”了。這是必然的結(jié)果,王敦不是個人,而是王氏集團(tuán),你“革”得了嗎?不怕傷了自己的蛋嗎?
歷史的規(guī)律告訴我們,最徹底社會進(jìn)步絕不是“中興”,而是以血為代價的改朝換代!
0個評論
文明上網(wǎng)理性發(fā)言,請遵守新聞評論服務(wù)協(xié)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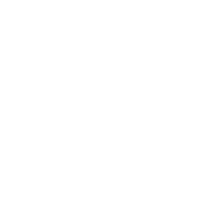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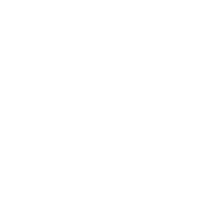
 魯公網(wǎng)安備37130202371693號
魯公網(wǎng)安備37130202371693號